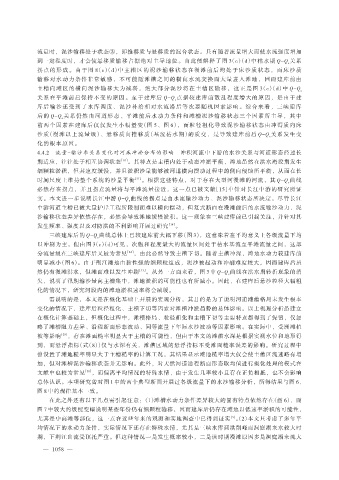Page 94 - 2025年第56卷第8期
P. 94
流量时,泥沙输移处于状态③,即推移质与悬移质的混合状态。只有随着流量增大而使水流强度增加
到一定程度时,才会使悬移质输移占据绝对主导地位。由此便解释了图 3(c)(d)中枯水期 Q-Q 关系
s
拐点的形成。由于图 8(c)(d)中主槽区的泥沙输移状态在漫滩前后均处于床沙质状态,而床沙质
输移对水动力条件非常敏感,不可能随滩槽之间的横向水流交换而大量进入滩地,因而建库前由
主槽向滩区的横向泥沙输移大为减弱,绝大部分泥沙将在主槽区输移,这正是图 3(c)(d)中 Q-Q
s
关系在平滩前后保持不变的原因。至于建库后 Q-Q 点据较建库前散乱程度增大的原因,是由于建
s
库后输沙还受到了水库调度、泥沙补给相对水流滞后等次要随机因素影响。综合来看,三峡建库
后的 Q-Q 关系仍然由河道形态、平滩前后水动力条件和滩槽泥沙输移状态三个因素所主导,其中
s
前两个因素在建库后仅仅发生小幅量变(图 5、图 6),而粒径粗化导致泥沙输移状态由冲泻质向床
沙质(漫滩以上流量级)、悬移质向推移质(基流枯水期)的质变,是导致建库前后 Q-Q 关系发生变
s
化的根本原因。
4.4.2 流量-输沙率关系变化对河床冲淤分布的影响 冲积河流中下游的水沙关系与河道形态经过长
期适应,往往处于相互协调状态 [10] 。其特点是主槽内处于动态冲淤平衡,滩地虽然在洪水淹没期发生
细颗粒淤积,但其速度缓慢,并且淤积沙量能够被河道横向摆动过程中的侧向侵蚀所平衡,从而在长
时间尺度上维持整个系统的沙量平衡 [21] 。根据这些特点,对于存在大型河漫滩的河流,其 Q-Q 曲线
s
必然存在拐点,并且拐点流量将与平滩流量接近,这一点已被文献[15]中针对长江中游的研究所证
实。本文进一步说明长江中游 Q-Q 曲线的拐点是由水流输沙动力、泥沙输移状态所决定。尽管长江
s
中游河道主槽已被大量护岸工程所限制而难以横向摆动,但复式断面在漫滩前后的水流输沙动力、泥
沙输移状态差异依然存在,必然会导致滩地缓慢淤积。这一现象在三峡建库前已引起关注,并针对其
发生频率、强度以及对防洪的不利影响开展过研究 [14] 。
三峡建库后的 Q-Q 曲线总体上已较建库前大幅下移(图 3),这意味着在平均意义上各级流量下均
s
以冲刷为主。但由图 3(c)(d)可见,次饱和程度最大的流量区间处于枯水基流至平滩流量之间,这部
分流量级在三峡建库后又最为常见 [24] ,由此必然导致主槽下切。随着主槽冲深,滩地水动力较建库前
明显减小(图 6)。由于荆江滩地由黏性强的细颗粒组成,泥沙被起动和冲刷难度较大,因而建库后虽
然仍有漫滩洪水,但滩面难以发生冲刷 [13] 。从另一方面来看,图 3 中 Q-Q 曲线在洪水期转折现象的消
s
失,说明了汛期输沙量向主槽集中,滩地淤积的可能性也有所减小。因此,在建库后悬沙粒径大幅粗
化的情况下,研究河段内的滩地淤积速率将会减缓。
需说明的是,本文是在概化基础上开展的宏观分析,其目的是为了说明河道滩槽格局未发生根本
变化的情况下,建库后粒径粗化、主槽下切等因素对滩槽冲淤趋势的总体影响。以上机理分析虽建立
在概化计算基础上,但概化过程中,滩槽格局、粒径粗化和主槽下切等主要特点都得到了保留,仅忽
略了滩槽阻力差异、沿程断面形态波动、同等流量下年际水沙波动等因素影响。在实际中,受洲滩植
被等影响 [29] ,存在滩面糙率明显大于主槽的可能性,但由于本文的滩槽水深是根据实测水位和地形得
到,而悬浮指标(式(8))仅与水深有关,滩槽区域的悬浮指标不受滩面糙率误差的影响。研究过程中
曾设置了滩地糙率明显大于主槽糙率的计算工况,其结果显示滩地糙率增大仅会使主槽区流速略有增
加,但对滩槽泥沙输移状态并无影响。此外,对天然河道沿程断面形态取均值进行概化处理的模式在
文献中也较为常见 [30] ,而偏离平均情况的特殊水情,由于发生几率较小且存在正负相抵,也不会影响
总体认识。本项研究曾对图 1 中的两个典型断面开展过各级流量下的水沙输移分析,所得结果与图 6、
图 8 中的规律基本一致。
在此之外还有以下几点需引起注意:(1)滩槽水动力条件差异较大的固有特点依然存在(图 6),而
图 7 中较大的级配变幅说明某些年份仍有细颗粒输移,因而建库后仍存在滩地以低速率淤积的可能性,
尤其是中高滩等部位,这一点在近些年来的观测和实地调查中已得到证实 。(2)本文只考虑了多年平
[5]
均情况下的水动力条件,实际情况下还存在特殊水情,尤其是三峡水库调洪削峰而洞庭湖来水较大时
期,下荆江出流受顶托严重。但这种情况一是发生概率较小,二是该时期漫滩原因多是洞庭湖来流大
— 1058 —